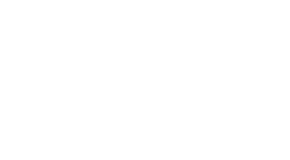网络直播诱导打赏涉嫌诈骗罪的辩护策略
摘要
针对采用虚假人设、固定话术、制造暧昧关系、虚假恋爱关系、以结婚为幌子等方式,编造虚假理由诱导非理性打赏的网络直播运营方,可能涉嫌诈骗罪。对此,无罪辩护策略可以被害人无错误认识为辩护切入点,以粉丝打赏与诈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作为辅助辩点。罪轻辩护要点主要包括准确认定诈骗数额、减轻退缴责任、“被害人”有违法目的和过错等。
关键词
网络直播 打赏 诈骗 无罪辩护 罪轻辩护
随着网络主播和直播平台的兴起,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也有诸多网络直播诱导打赏行为被判定为诈骗罪。是否一律构成诈骗,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区分行为类型,有许多争议问题,值得讨论。
一.网络直播诱导打赏的行为特征
网络直播的全称系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即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注册账号、开设直播间,向网络社会公众开展各种主题的直播营销活动,如“吃播”“带货直播”“娱乐主播”等等。其中,网络直播活动涉及的几方主体主要包括直播营销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从判例来看,被认定构成诈骗罪直播营销活动参与者主要包括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对于直播营销平台、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则因为行为分工不同而并未涉及诈骗。
直播间运营者与直播营销人员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打赏或者其他各种经济利益,往往使用各种营销手段获取粉丝、受众的关注,进而通过各种套路获得打赏等经济利益。其中,常见的违法违规营销手段主要包括低俗团播引诱打赏、虚假人设诱骗打赏、诱导未成年人打赏、刺激用户非理性打赏等等。司法实践中,主要涉及诈骗罪的集中体现在虚假人设诱骗打赏、刺激用户非理性打赏。其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几个特征:
一是虚构人设。即隐瞒已婚而谎称单身,营造“贫困户”“王妃”“精英海归”等虚假人设,冒充空姐、教师、医护人员等特殊身份,或使用AI技术生成虚假肖像,诱骗观众打赏。
二是固定话术。直播运营方或者播主预先设计一整套的营销聊天话术,用来作为模版与不特点的粉丝受众进行沟通交流,如“马甲话术”“女神话术”等。
三是非主播人员代聊。因为播主无法同时与多名粉丝一对一互动,于是直播运营方便设立专门代聊人员,冒充播主通过聊天工具依据固定话术与粉丝进行一对一的互动交流。粉丝以为自己在与播主聊天,实则其他代聊人员。
四是制造暧昧关系,虚假恋爱关系,以结婚为幌子。直播的播主假装与粉丝谈恋爱、交朋友,暗示性行为等方式,使得粉丝陷入错误认识,幻想与播主可能存在自己所希望的关系,进而导致粉丝非理性打赏。
五是编造各种虚假理由等方式诱导非理性打赏。直播营销方与播主往往假借各种借口,如线下见面、差旅费、虚构“输了人气PK赛会受惩罚”、对打赏粉丝进行排名、设计“打赏入股”玩法、利用“狗托”虚假刷礼物烘托气氛等方式,进而刺激粉丝用户进行非理性打赏。
可见,通过上述对网络直播诱骗打赏行为的解构,网络直播运营方以及播主是完全可能涉嫌诈骗罪的,也确实存在大量的司法判例。但是,事无绝对,并不能脱离个案的细节而笼统地全部将网络直播诱骗打赏行为进行泛化认定。针对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涉刑问题,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脱离证据和事实的有罪推定。
二.网络直播诱导打赏涉诈骗罪的辩护策略
针对此类案件,试图从诈骗罪客观要件去辩护,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策略。通常来说,由于网络直播的极端推广特征,通常存在夸大其词的成分,甚至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客观情况。即便是有些夸大宣传,尚不能完全确定构成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是由于界限并不清晰,进而导致容易被有罪化。故而,试图否定存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一般不能成为有效的辩护要点。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直播过程中,所采用的话术并没有明显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是通过一些容易引发联想的模糊性表述,理论上说也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诈骗客观行为。这种认定易会引发争议,也很难完全依托这一点来达到辩护效果,需要结合其他辩点共同发挥作用。
有效的辩护,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切入和展开。
1.被害人无错误认识是辩护切入点
网络直播作为连接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媒介,并不能完全按照现实社会逻辑去理解和认定。粉丝们对主播的喜爱,有时候是非理性且狂热的。这种非理性的喜爱并非是基于错误认识而产生的,而有时候是基于主播的特殊魅力、特殊容貌或者其他稀有特征而产生的。这个时候,粉丝并没有陷入错误认识,而甚至于在明知主播有虚构人设或假装恋爱的情况下,仍然对主播“不减所爱”。实践中,也出现过粉丝在接受调查时,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也明知主播同时在与多个异性粉丝进行交往,也明知主播虚构人设、玩暧昧,依然还是喜爱这个主播。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有其主播个人魅力的因素,并不能完全否认主播个人的价值贡献,完全归于粉丝陷入了错误认识而产生的非理性情感表达。
针对长期打赏的粉丝,对网络直播的运营套路也非常熟悉,并无一无所知。一些有经验的长期混迹于网络直播圈的老粉丝,也是同时关注并打赏多个主播。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认定这类粉丝存在错误认识。
2.粉丝打赏与诈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可作为辅助辩点
具体个案中,往往存在所谓粉丝自愿打赏的情况,即粉丝打赏与诈骗行为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粉丝之所以自愿打赏,原因可能很多。既存在因主播实施诈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进行打赏的情形,也存在因为主播为粉丝提供了情绪价值而粉丝认为值得打赏的情形。可见,粉丝之所以打赏,也并非完全是因为被主播或者网络直播方诈骗了,也完全基于情感回报的正常奖赏等合法情形。在后一种情形下,即便主播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也并不能直接认定粉丝的自愿打赏行为就是这个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所导致的,仍要针对粉丝打赏的原因进行展开调查。粉丝打赏的真实动机和诱因,也完全可能存在其他理由,而不宜将主播的诈骗客观行为特征直接认定为粉丝打赏的原因,二者并非直接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不必然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实操中,存在粉丝在明知主播存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大额的打赏、送礼物等行为。正所谓,人在恋爱中有时并不完全理智。即便认为这种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有一定缝隙,判定其为犯罪行为也需慎重。
对此,有观点认为,直播打赏的自愿性应以“信息真实”为前提,从业者通过欺骗手段骗取打赏的将构成诈骗罪。这种观点实则偷换概念,否定了诈骗罪的固有构成要件要素。直播打赏的自愿性与直播所展现的信息是否真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不管直播所展现的信息是否真实,直播打赏都有可能是自愿的。即便是直播存在虚假信息,并不意味着粉丝就有相应的错误认识。如果粉丝不存在相应的错误认识,而粉丝基于自己的非理性,所实施的直播打赏仍然可以是自愿的。过分强调直播信息的真实性,并仅仅因为直播方采取了所谓的欺骗手段就认定从业者构成诈骗罪,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即片面强调和刻意拔高直播方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特征,而忽略了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而支付财物等诈骗罪其他要素的判断,本质是否定了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素。这显然是不周延的犯罪认定逻辑。
3.准确认定诈骗数额以从轻辩护
具体个案中,诈骗数额认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简单依据网络直播方的收款流水认定诈骗数额;二是平台抽成部分是否应计入诈骗数额、违法所得。上述这种认定方法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一是不宜简单依据网络直播方的收款流水认定诈骗数额。由于调查难度,往往无法做到对所有的打赏粉丝进行全面调查,针对没有调查的部分数额并不能认定为诈骗数额。未经调查情况下,并不能确定其他打赏者就一定存在错误认识,进而不能认定构成诈骗损失。从证据链角度来看,网络平台一般会将预收的打赏资金混在一起,定期划拨给网络直播运营方。因此,这种情况下,仅仅依据网络直播方的收款流水,并不能确定这些资金的具体来源,无法确定是否被害人的损失。此外,针对诈骗罪这种明确存在被害人的刑事法律关系中,是需要被害人的明确具体陈述的证据。换言之,应将结合被害人陈述、转账流水、收款流水、打赏记录等多个证据予以确定诈骗数额。
二是平台抽成部分应计入诈骗数额,但不应苛责直播方退缴。网络直播平台虽然一般情况下并不能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但是确实为直播运营方提供了直播平台的技术条件及用户资源,客观上促成了诈骗犯罪。因此,实践中直播平台对打赏钱款抽成一定的比例,高的有50%以上的比例。这就导致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中的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资金被直播平台分走了,并没有被网络直播运营方实际所得。是否将这部分钱款认定为诈骗数额,有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直接成本,应一并计入犯罪数额。理论上来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针对网络平台的抽成,也确实属于诈骗行为人为了获取诈骗所得的成本支出。但是,诈骗数额的认定并不完全等同于退缴责任的认定。如果要求网络直播运营方连带退缴被平台抽成的部分,而平台反而没有任何退缴责任,这是显然不公平的。网络直播平台显然不能以善意取得或者主观没有过错,回避赃款的退缴责任。这部分资金显然属于犯罪赃款,应依法予以追缴,而追缴应该按照“谁获得谁退缴”。一方面放纵追缴平台实际所得的赃款,而另一方面强行苛责网络直播方连带退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即便实操上,无法责令网络平台予以退缴所抽成部分,但是也不应追究网络直播运营方对此部分抽成资金的连带退缴责任。换言之,应按照网络直播运营方的实际所得予以确定追缴退赔的范围。
4.“被害人”有违法目的、过错可作为罪轻辩点
部分网络直播的粉丝,在关注主播后,试图与主播发生不可告人的关系,甚至于带着“嫖娼”的非法意图与主播交流,实在难以被认定所谓的诈骗罪“被害人”。这种所谓的“被害人”从一开始便有不良动机和违法目的,在与主播接触后,通过打赏试图达到自己的违法目的,但是目的一旦未能得逞,便控告主播为诈骗。针对这种情况,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直播方有“将计就计”而顺势实施诈骗的可能,也确实存在涉嫌诈骗罪的可能,但是同时也说明这里的“被害人”存在过错和违法目的。针对这种情况,对网络直播方苛责,无可厚非,但是并不宜完全站在“被害人”一边,而应对网络直播方进行从轻处罚,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