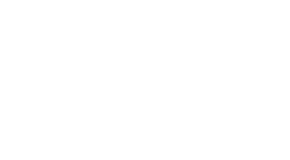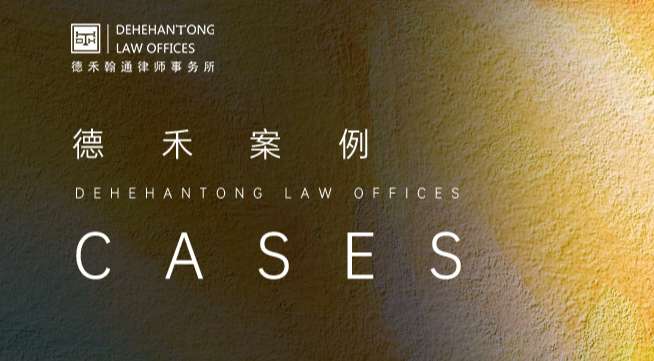成渝金融法院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之初探
以“委托理财”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成渝金融法院公布的判决书共有五份,均为上诉案件。其中,三份所涉案件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另两份所涉案件系同一上诉人(原审被告)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下面笔者试从保底条款的效力、委托理财与民间借贷的区分以及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等方面,通过这四个案例来探究成渝金融法院对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
鞠某强与周某、刘某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2023)渝87民终4394号
案例一
周某与鞠某强签订《委托证券投资协议书》,约定周某将自有资金450万元的证券账户全权委托给鞠某强进行投资证券。鞠某强负责买卖,周某不参与买卖和建议。鞠某强对周某本金450万元承担保本责任且投资本金利息按年化率6%计算,证券投资结算的投资收益(超过投资本金利息部分)由双方各分50%,若结算时的投资收益为负时,由鞠某强补足本金及利息。
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届满后,投资出现巨额亏损,自愿出具《还款承诺书》向周某承诺还款4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鞠某强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证明鞠某强因自身过错造成委托人周某损失,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系其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支持原告周某要求鞠某强支付赔偿款之诉请。
梁某华与曾某、杨某芬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2023)渝87民终1666号
案例二
梁某华经杨某芬、曾某介绍,在某投资理财平台投资,向指定的收款人转款共计66,600元。杨某芬和曾某在微信群里宣传、介绍该平台并帮忙充值。后,该平台关闭、无法提现。
一审法院认为,梁某华的举证不能证明其与杨某芬、曾某建立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唐某与傅某翔、谢某颖等合同纠纷案
——(2023)渝87民终6935号
案例三
傅某翔与唐某通过微信聊天,唐某提出让傅某翔出资20万元用于炒股,并承诺年化收益不低于10%,傅某翔按照唐某的指示将20万元转至杨某的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傅某翔与唐某建立了委托理财的合同关系,故判决唐某向傅某翔支付委托理财款本金17万元、收益15,000元和相应资金占用损失。
中国某银行某支行与朱某容/杜某玉
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2024)渝87民终942号、(2024)渝87民终4986号
案例四
某信托公司制作某XX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某XX集合信托”),并发布了相应说明书,某银行与该信托公司签订某XX集合信托资金代收代付协议,由信托公司委托该银行在信托计划发行期间代理信托公司向信托计划委托人收取委托资金。银行按照信托公司制定的信托计划及相关文件的内容向信托公司推荐合格投资者,并不得有任何承诺最低收益的意思表示。上述协议签署后,该银行支行工作人员游某静向朱某容、杜某玉等人就某XX集合信托进行了推介。
朱某容向第三人钟某春账户转款20万元,双方签订《合作投资协议》,后者根据前者等多人的委托,共集资540万元,以自己的名义作为信托产品的委托人与该信托公司(受托人)签订《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认购信托计划540万元。杜某玉向第三人邹某账户转款30万元,双方签订《合作投资协议》,后者根据前者等多人的委托,共集资470万元,以自己的名义作为信托产品的委托人与该信托公司(受托人)签订《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认购信托计划470万元。钟某春和邹某均以投资人身份签署了《投资人声明书》。
后,钟某春和邹某所代表的投资人因无法收回投资,经信访,重庆银保监局出具了书面答复意见书,认定:某XX集合信托系依法合规设立的信托产品,某银行作为信托计划的代理资金收付银行,受委托向合格的投资者推介信托计划。该银行员工在代理销售信托产品时存在归集客户资金投资信托计划的情况,违反《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的规定。
一审法院判决该银行赔偿朱某容/杜某玉投资本金以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的70%。
01、“保底条款”的认定和效力
保底条款是指,无论委托理财盈亏与否,委托人均收回部分或全部投资本金甚至取得收益的条款,形式不限于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或是签订单独的保底协议或出具承诺书等。笔者认为,保底条款的本质是委托理财合同双方对投资结果可能性所产生风险的再分配。
在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一般会认定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无效。这主要是考量以下三方面:
1、保底条款约定受托人承担非因其过错造成的损失,与《民法典》第929条所规定的委托合同关系的损失赔偿原则相左。
2、保底条款免除了委托人本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使受托人负担了不对等的义务,违背了《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公平原则。
3、禁止“刚性兑付”是“资管新规”等规范性文件针对金融机构的要求,“九民纪要”中也对金融机构的该行为给予否定评价,尽管并无法直接约束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但对其亦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引作用。
在案例一中,亏损由鞠某强负责补足的约定实际上排除了周某在投资活动中的全部风险,将金融市场投资风险不合理的全部分配给受托人鞠某强承担,属于投资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
由于该条款不合理地分配金融市场投资风险,诱导投资者误判投资风险,非理性地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不断积累和放大投资风险,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最终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故该保底条款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
另外,至于鞠某强出具《还款承诺书》时,《委托证券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委托期限已经届满,他对亏损的事实清楚知悉,与在签订《委托证券投资协议书》时无法判断盈亏即承诺“保底”的主观认知有明显区别,并不会导致投资者误判或漠视投资风险,不会发生引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也没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系鞠某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该《还款承诺书》合法有效,应当约束鞠某强。
本案最终经成渝金融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可见,事后签订的《还款承诺书》并非双方对投资结果不确定性的分配,不属于“保底条款”,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应当受其约束。
02、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与民间借贷的区分
委托理财是受托人按照约定管理委托人的资产,从而获得一定报酬或者分红。而民间借贷则是当事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双方的合意是拆借资金。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双方订立合同时的实质目的:如果合同的实质目的是资金拆借则属于民间借贷合同,如果实质目的为委托理财则属于委托理财合同。
合同中没有明确表达双方真实目的的,就需要探查双方在合同行为中的客观表现,结合其约定、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惯例来判断。
在案例二中,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委托理财合同,梁某华仅能举证证明杨某芬和曾某在微信中对该投资平台有过宣传介绍以及代为充值的行为。杨某芬和曾某在收到梁某华的款项后均根据梁某华提供的平台账号和密码按照梁某华的要求充值到投资平台,梁某华自主选择该投资平台推介的所谓理财产品。上诉人梁某华并不能举证证明其与杨某芬、曾某之间形成了委托理财的合意。
因此,成渝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案例三中,唐某提出让傅某翔出资20万元用于投资股票,并承诺年化收益不低于10%,但并未约定投资的具体标的以及如何结算,傅某翔是否可以参与、监督投资活动,投资的盈利分配、亏损承担等问题,双方关于委托投资理财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
通过双方协商以及履行来看,唐某与傅某翔之间实际是唐某要求傅某翔交付资金,由唐某完全自行处置资金,傅某翔不参与投资活动,对资金使用没有任何权利,最终由唐某还本付息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款合同关系。
双方之间并未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且基于“无权利则无义务”的法律逻辑,傅某翔在唐某占有使用其资金期间,对资金使用情况完全没有任何权利,由傅某翔对唐某所称的亏损承担责任,显然与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匹配,也与唐某多次承诺归还本金并支付收益的意思表示不符。因此,成渝金融法院认为,原判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这两个案例通过双方提交的客观证据来对其真实意思表示与合同目的进行判断的。案例二是上诉人(原审原告)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委托理财关系的诉请;案例三则是通过证据分析得出其“实为借贷”的本质。
03、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中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
案例四中,某XX集合信托在发行时系合格的信托产品,某信托公司亦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某信托公司知晓某XX集合信托在销售时存在违规汇集资金情形,因此某信托公司不应该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某银行学府路支行不仅提供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点获取佣金,更是以出售自己的信用与巨大影响力的方式获取佣金收入,若其在获取收益后完全不承担对客户的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某银行学府路支行与某信托公司之间除代收代付关系外,还深度参与某XX集合信托的推介和销售。作为某XX集合信托的代销机构,某银行学府路支行并非仅仅为案涉产品的买卖双方提供平台和渠道,还利用朱某容/杜某玉等投资者对自己的信赖,通过积极营销的方式推动投资者购买某XX集合信托。
适当性义务系销售者法定义务,与销售方式无关,谁负责销售金融产品,谁承担合理推荐与适当销售义务。某银行学府路支行不能以自身非产品管理者或发行人主张免除基于适当性义务的要求与责任。
成渝金融法院认为,“卖者尽责”是“买者自负”的前提,某银行学府路支行明知朱某容/杜某玉等人系非合格投资者,违规汇集资金购买与其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当的金融产品,从而导致投资者作出不合理的投资决策,造成资金亏损。因此某银行学府路支行履行适当性义务是朱某容、杜某玉等人自行承担责任的前提,其负担赔偿责任是因此过错行为对杜某玉造成损失后的弥补,与约定无论何种情形下都保底保息的刚性兑付无关。
另一方面,信托计划不同于普通的理财产品,其投资回报率较高,相应的投资风险亦较大。朱某容、杜某玉作为具有多年投资理财经验的投资者,在明知其系某XX集合信托非合格投资者的情况下,为追求高收益与其他投资者集资购买某XX集合信托,其自身对案涉产品的亏损亦具有一定过错(30%)。
因此成渝金融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4、结语
对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案件,成渝金融法院的案例样本并不多,但所公布的这几个案子也反映了此案由中较为典型的争议点。
尤其是案例一,该案系通过审委会讨论后作出的判决,较能体现该法院的官方立场。以及案例四,还涉及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行中信托公司、代销银行和委托人(名义投资者)、被代持人(实际投资人)等多重关系的处理,让我们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准确把握,颇有裨益。